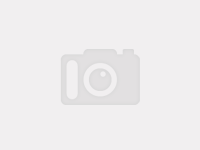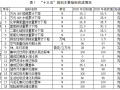曹旭升律师|为矿所困的矿奴
- 2022-05-29 17:20:27
- 来源:公众号:法言矿语
- 作者:曹旭升律师
- 0
- 0
- 添加收藏

上月出差办案,听曾经做铁矿的李总讲述自己如何下海做矿,一开始顺风顺水后来负债累累给人打工的艰辛故事。团队律师陈孝劲博士当时送其一个名词:矿奴。
这些年,房奴几乎人人皆知,但矿奴,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什么是矿奴呢?听着陌生,但细细琢磨,90%的矿业人能对号入座。
我本人,1998年就以书记员身份参与过涉矿案件审理,2008年就办理了第一个涉矿案件,2010年开始专门学矿业,2015年专职做矿业律师,长期处于矿业纠纷的漩涡之中。看到35号文不利于矿业发展,看到矿法修改不尽人意,不断呼吁,耗时费力不讨好,但仍乐此不疲;给濒临破产的民营矿企服务,收不上费,有时基至赔钱,不论收不收费,都要第一时间灭火消灾;给国有矿企服务,竞标比选,被挑来挑去,律师费被压到最低,还要逆来顺受好好服务;给政府做顾问,拼大所门面,拼个人业绩,拼团队奉献精神,最终能否被聘全靠过关斩将真实力,干不好,还要承担责任;做矿业律师,不但懂法还要懂矿,更要懂如何将矿业法律、矿业技术、跨界思维、国学理念、处事能力、办案经验等等融合在一起,这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融入矿业圈层,动笔写、开口讲、到处跑,筋疲力尽。仔细品味,哪个矿业律师都得学习、奋斗、吃苦、忍辱、屈就,显然,包括我在内的矿业律师们,几乎都是被矿所奴役的矿奴。
民营企业做矿,往往取得矿业权时就花光了全部积蓄,探矿、建矿都需要融资,而民营企业本身融资难,矿业民营企业融资更难。融不到资或融资额不够,就探不明、转不了采、建不了矿、开采不了、还不上账。若矿权在,维护矿权每天就会产生成本,所欠债务利息逐日增加,这样负债越来越高、融资越来越难,既开采不了,又卖不出去,进退两难。若矿权灭失,则债务缠身,无钱还账,官司不断;跑不了,死不了,活不起;轻则名声扫地,中则失信限行,重则锒铛入狱。这样的矿业权人被矿折磨的生不如死,是典型的矿奴。
那些资本充足的民营矿企,取得了采矿权,建了矿,采出了矿,有了现金流,甚至日进百万千万,看着舒服。殊不知,这些矿业权人要不断应对各种新情况、新政策、新要求。绿色矿山不达标,智能矿山未改造,应对双碳未规划,随时面临关、停、并、转;别人出了事故,你要停下来;你若出了事故,要关停,至少整改;生产规模小了,要资源整合,要技术改造,改造期间只花钱不进钱,不得生产;原来剥离物没有价值,存放有成本更有环保风险;现在剥离物能做机制砂、能综合利用了,但各地要重新评价、集中处置,都需要向国家另行交钱。转采、延续、增储、整合、技改,处处花钱,处处审批,处处耗时,稍有不慎,则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环境污染、非法用地、非法采矿等等,轻则警告罚款,中则关停整改,重则刑事立案。这样的矿业权人,因为矿,危机四伏、寝食难安,是表面风光内心苦涩的矿奴。
那些上市的矿业企业,一个事故、一个污染、一个新应用、一个超级矿投产、一个政策调整、一个信息披露不实等等,就可能引起股价动荡,就可能影响正常经营。近日锂的上涨、镍的妖风、期货的无情、资本的兴风作浪,让一个个上市的矿业公司如履薄冰、闻风丧胆。上市的矿业权人,犹如被公开示众,没有隐私,被市场行情、被隐形之手、被国际形势、被舆情等等操控,是被扒光了的矿奴。
那些国有矿业企业,一个决策、一个交易,就可能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黑锅;风险把控不好,要追责;乱作为,要追责;不作为,要追责;未尽社会责任,地方政府不待见;尽了社会责任,成本增加业绩不好;各种保护地退出、各种建设项目压覆,要补偿,不讲政治;不要补偿,没法做账;打官司,影响不好;不打官司,权利受损。这些国有的矿业权人,往往是被体制束缚或心甘情愿的矿奴。
矿业企业的上下游企业,随着矿业的好坏随波逐流。矿业景气了,定单不断,相当于工蚁,不断劳作;矿业不景气,转行则生死未卜;不转行则举步维艰。这些企业,大多是依附于矿业的寄生矿奴。
涉矿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各项职能随着矿业政策的调整而调整。尤其放管服之后,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不行;不管,不行。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到位、放权不到位、改制不到位,或者面临各种监督,或者被告上法庭。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矿业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为矿企服务的公仆意识,随时会面临各种投诉、追责,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矿政管理人员或矿业人,必须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必须受各方的监督,这些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矿业人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必须保障矿业法律制度得以正确实施,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打着引号的“矿奴”。
2021年12月,中央会议首次将矿产与能源相提并论,提出能源矿产安全,意味着矿产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2022年2月,人民日报评论部将矿产和农产品相提并论,提出矿产是初级产品,要求必须保障初级产品供应。这说明矿产的重要性正在得以彰显,“矿奴”们即将迎来春天。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法言矿语
作者:曹旭升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