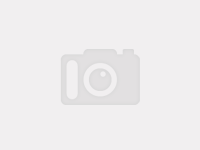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二)
- 2020-06-16 10:29:32
- 来源:《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9-3期
- 作者:潘云唐教授
- 0
- 0
- 添加收藏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发于《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9-3期
上文链接:
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一)
从北京大学到北京地质调查所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黄汲清一直心向光明,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和抵制,又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的各种活动,但他同时也非常认真地学习,争取优异成绩。1928年6月,他和同班的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四人通过考试,都获得了毕业证书。
就在他们毕业的前几天,李四光老师在家中设冷餐会招待他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也在座。这个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地质机构,先后隶属农商部、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工商部,对外则称“中国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大家一边吃着冰淇琳,一边讨论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翁先生欢迎他们去地质调查所。李先生说中央研究院要开设地质研究所,他下半年要南下到上海去筹建还要亲任所长,又说朱家骅先生已在广州办了两广地质调查所,也欢迎他们去。可见中国早期培养的地质人才是稀缺资源,丝毫没有“毕业就是失业”的危机感。当时,在李先生家,又当翁先生之面,他们四人就初步商定黄、李去北京地调所,朱去地质研究所,杨去两广地调所。
黄汲清和李春昱毕业之后,先按翁先生要求去填绘一幅1:25000地质图,以代替入所前之考试与实习。这幅图包括了北京西山的碧云寺、香山、八大处等地,这次工作他们都有很大的收获。朱森去上海前又和黄汲清一起考察研究了北京西山的羊坊花岗岩、刁吉山火山岩。8月份他们结束野外工作返北平(现北京)时,朱森就要要去上海工作了,黄汲清特赠他一本书,以作临别纪念,并题诗一首:
四载相亲似弟兄,登山涉水总相从。
何堪一旦别离去,谈天说地谁与同?
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
但愿脚踏额非尔士之顶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云横秦岭家即在,巫山巫峡乐无穷。
暂别莫效儿女哭,他年天涯海角、海角天涯总相逢。
相逢再话燕都事,那时切莫忘了汽水一瓶,啤酒一盅。
虽然黄汲清谦虚地把这首诗称作“打油诗”,但它铿锵的声调、风趣的比喻、热诚的倾诉和奋发的激情,充分表达了这两位同学在为崇高事业的征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1928年9月1日,黄汲清正式到北平地质调查所上班,令人没想到的是,翁文灏所长竟然把黄直接安排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工作,黄的办公桌就与翁的秘书之办公桌挨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刚来的练习生(还不是正式的调查员)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这显然是翁对黄这样特殊的、杰出的高材生已有了深刻的印象。黄汲清不论功课还是野外实习,成绩都很优异,特别是学生时期就在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并荣获该所设立的“学生奖学金”。而且,几个月前,翁带领黄等同班四人到热河省北票煤矿进行野外实习,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大家的又加深了了解。黄虽然对翁的特殊安排感到欣慰、自豪,但他同时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所长的眼皮下办公,我的尴尬心情、局促不安可以想见”。
黄汲清到地质调查所不久,就奉派与王竹泉一起去东北调查煤田。他们先乘火车到天津,后转乘海轮到大连,又换乘南满铁路的火车到了奉天(即今沈阳),王竹泉安排他先去奉天东南的本溪县太子河流域的小市煤田。他乘火车到了本溪,再骑毛驴到小市,到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他用平板仪测地形图,又初步查明了寒武奥陶系和含煤的石炭系地层之关系。五六天后,王竹泉又打电话告诉他,小市工作不要继续了,让他快回奉天。他匆匆结束了小市工作回到奉天,见到王竹泉时才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西边热河省的阜新煤田进行勘测。
黄汲清随王竹泉从奉天乘火车到锦州,再转车到热河省阜新县的八道壕煤矿。他们骑马横穿煤田两次,初步了解到煤田的构造轮廓和煤系地层分布范围。黄用平板仪测量地形图,王主要查明地层层序,在地形图上勾划出煤系地层界线。然后黄随王下煤井勘查地下地质和煤层分布,并采了煤岩样品,半月后完成了阜新煤田地质图。当年12月,他们回到北平。他们首先从事室内整理,编写正式报告,清绘地形地质图及各种图件,又把采集的很多化石(主要是古植物)对照《中国古生物志》等文献进行初步鉴定。他们原认为阜新煤系属中侏罗统,后古植物专家修改为上侏罗统,甚至有专家认为是下白垩统,而随着古生物地层学的发展,最近更多人更倾向于认为是下白垩统。
这次野外工作的成果被正式整理成中英文研究报告,黄独著的有“奉天省本溪县小市煤田地质的初步报告”,与王(第一作者)和著了“热河省阜新县煤田地质”,2个报告都于1929年发表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系列研究报告集《地质汇报》第13号上。
1929年春,黄汲清又接到新的任务,就是随赵亚曾一起从北平去西安,翻越秦岭南下四川进行地质考察。赵是黄北京大学的学长,又是助教老师(主要辅导古生物学课程),同时还是北平地质调查所的技师兼古生物研究室负责人之一,接近而立之年就出版作品数十种,真是“著述等身”,尤其是五本大部头经典巨著——《中国古生物志,乙种》,其中的代表作——《中国的长身贝科化石》(上下卷)以内部构造为分类依据的重要观点,在几十年内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深得国内外地质界崇敬。黄汲清对这位良师益友非常尊重,与他一起出差深感荣幸。
赵亚曾与黄汲清雇用了北平昌平县一位小伙子赵承佩给他们当临时工、服务员,他们乘火车经京汉、陇海铁路到河南陕县,再转汽车到西安。他们在西安先拜会了陕西省长宋哲元的秘书长,递上介绍信,希省府发文沿途各县政府对他们进行保护,并提供各种方便。3月15日,他们从西安向南翻越秦岭到柞水、镇安等地工作了几天,后又回西安向西行到宝鸡,向南经大散关翻越秦岭,在凤县盆地、汉中盆地工作。他们为了多做一些工作,多获得一些资料,有时也分头工作。5月中旬,他们在陕西略阳县工作告一段落后,赵亚曾就独自一人顺嘉陵江南下,相约在四川广元县朝天镇会合。黄与赵承佩向东南,经大安驿到陕西宁羌县(今宁强县),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晚11点左右,听说大股土匪攻打县城,在南门与民团对峙。黄与赵承佩藏好行李物品,和老百姓一起,跑出北门,又找个小客栈住了一天,后来听说土匪被打跑,他们才跑回原旅馆取了行李,向西南行。到了朝天镇与赵亚曾会合,说起前一天的惊险,都表示要更加谨慎。
黄汲清与赵亚曾等在四川广元未多停留,又顺嘉陵江支流白水江向西北考察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山区,直到甘肃文县的碧口镇,再往南到四川青川县,然后沿涪江河谷南下,经江油县而于当年6月初到达成都。在这里他们遇见北大老同学黄鹏基(在《川康日报》当编辑)。黄鹏基在《川康日报》上发表了新闻报道,介绍了赵亚曾、黄汲清二位地质学家的履历及这次来四川从事地质工作的简况,这既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也引起四川乡亲对地质事业的重视和兴趣。
他们要在成都休整一段时间,于是黄汲清就向赵亚曾请假回离别八年的故乡仁寿县。他乘滑竿回到仁寿县青岗场家中,见到堂屋左侧供奉着父亲的灵位,他一下子昏了过去。回想起父亲为他的前程操劳,含辛茹苦筹措学费,总希望有天能与父母亲人团圆,可惜老父已逝世,子欲养而亲不在,实乃人生一大憾事,他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大哥将他扶起入座,老母也来,大家悲喜交集,相拥而泣。后他被告知,父亲去年春病故,临终前还叫人翻出他的旧衣衫并反复端祥,当时他正值大学毕业关键时期,为不影响他的学业家人才未告知。
黄汲清回到成都后,赵亚曾对他谈起在成都休整期间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花了五六天去峨眉山把这个“天下名山”的新老地层顺序弄清楚了,又去成都北边的彭县(今彭州市)考察白水河铜矿,还发现了从西北方向朝东南方向逆推于煤系地层之上的“纳布构造”。黄很是佩服,他是较早确认中国境内有阿尔卑斯构造的地质学家。
当年9月,他们还溯岷江而上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汶川、茂县考察了10多天,回到成都后,又到自流井地区考察,研究了那里的中侏罗统地层(后来被命名为“自流井统”),特别考察了那里的盐井和“火井”(天然气井)。
10月中旬他们到了叙府(今宜宾市),这里是长江上游金沙江和支流岷江的汇合处,是川南的一个大城。他们收到丁文江等寄来的信和材料,告诉他们北平地质调查所已成立以丁文江先生为首的西南地质矿产调查队,9月从北平出发,乘火车到汉口,再乘轮船到了重庆,赵、黄二人比他们早出发半年,作为他们的先遣队,现在就算一个大的项目队了。丁先生信上商量工作,认为现在会合在一起,安全也有了保障。赵亚曾说中国各地不安全的地方还很多,假若仅为了安全,那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现在最好还是先分头工作,取得更多资料,做出更多研究成果,以后再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和需要,在适当地方会合起来干更大的项目。
黄汲清随赵亚曾在叙府停留了一段时间,考察了宜宾附近的地质情况。然后赵安排黄一人先到云南镇雄,再向东去贵州先与丁文江等会合,赵亚曾则与赵承佩直接南下,乘川滇铁路先去云南。黄从宜宾向东南于11月底到了四川永宁(今叙永县),却接到赵承佩寄来让邮局留交的快信,说赵亚曾11月15日夜在云南昭通闸心场被土匪开枪打死。黄一看泪水直流,回到旅店更大哭一场。他立刻发了两封电报,一是给正在旅行考察的丁文江先生,告知赵遇害之经过。另一是给云南省主席龙云,略称:“北平来的政府特派员赵亚曾先生,在贵省昭通县闸心场被土匪枪杀,请速派得力部队追捕匪首,……。特派员黄汲清”。
黄汲清迅即经贵州飘儿井赶到大定(今大方县)面见丁文江。他首先说起赵亚曾遇害一事,丁非常难过,泣不成声,黄与其他人也难过掉泪,约10多分钟后,大家才平静下来。丁先生身边工作的有二人,一是测量学家曾世英(江苏苏州人,年纪30岁,身材瘦小却很健壮,很能干),另一是地质采矿专家王曰伦(山东泰安人,与黄汲清年龄相仿,也很精干)。丁文江先生说,赵亚曾先生之死,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我们西南地质大调查中的川广铁路勘线工作才开始,更多工作还在前头。他们在一起工作不久,翁文灏所长发来电报,称黄汲清出外工作已近一年,可回北平休息了。黄回电说他不需要休息,愿随丁先生一道工作,绝不半途而废。这种以工作为重的崇高精神,不仅加深了翁文灏对他的器重之情,也使丁文江、曾世英、王曰伦等非常钦佩和赏识。
丁文江一行从大定向东继续考察,在贵州西部一带见有含双壳类化石的灰岩盖在二叠纪煤系地层之上。他们再往东行,发现构造复杂、断层很多,地层不连续,难以追索,化石稀少,不好对比,特别见一层硅化灰岩,其中找不到化石,按以往经验,有点像贵州的震旦纪灰岩。晚上丁文江与黄汲清、王曰伦讨论时,低头沉思道:“那个震旦纪硅化灰岩似乎拿不稳,弄不好会丢我们三位大地质学家的人!”黄汲清同意丁的看法,愿再仔细观察,又经过两天的努力,他们终于在薄层硅化石灰岩中找到小型双壳类化石,确人了它与黔西其他地方一样是属于三叠纪的石灰岩,丁文江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在黄汲清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除考察地质矿产外,也进行人种学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多,逢赶集之日,丁文江等就请来很多老乡,用皮尺量身高,用椅子量坐高等,回北平后,再整理研究发表。
丁文江领着曾、王、黄等到了贵州省会贵阳市,省主席毛光翔是军人,他很敬重中国的地质学家,特别派人迎接丁等进城,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和晏会。毛光翔主席致欢迎词,丁文江也致了答谢词。他们在贵州游览了名胜古迹,丁又派黄汲清和王曰伦调查了贵阳城郊的煤田。后来丁又与曾世英、王曰伦继续考察川广铁路线的黔南都匀、独山和桂北的河池南丹一线,让黄汲清再去贵阳西北的安顺、织金等地,搜集更多的资料。
黄汲清到了安顺市,先考察著名的螺蛳山。他发现薄层灰岩中有保存完好、精美的螺蛳(腹足动物)化石,以前有人认为它是第三纪湖相沉积的,黄发现这层含精美化石的灰岩和附近大面积的三叠纪灰岩是整合接触的,而且那些螺蛳化石经仔细鉴定也和三叠纪的属种相同或相近,故而确定为三叠纪灰岩,黄在这里做了很好的订正。
黄汲清从安顺往北,到了黔中高原的织金县,这里主要有二叠纪的灰岩和煤系地层。他去拜访县长,县长热情地和他谈起北京各大学的情况,一起聊天的还有一位老人,谈起来方知他是北大地质系学长丁道衡的父亲,黄亲切地称为丁伯伯,丁伯伯的父亲、丁道衡的祖父丁宝桢就是赫赫有名的“丁宫保”,清末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特别是在四川做了很多好事,深得民心。幸会丁伯伯是黄的一个重大收获。
黄汲清后来向南折返安顺,又向东回到贵阳,等待丁文江等返回,结果,丁、王、曾在黔南都匀、独山考察泥盆系、石炭系很有成果,采了成吨的化石,又继续深钻下石炭统(就是后来建立的“丰宁系”),就暂不返贵阳,丁指示黄过完春节后由贵阳向东再作路线调查。黄过完春节后就从贵阳经龙里、贵定、平越(现福泉县),再向东北经黄平、余庆,再向西到瓮安、开阳,最后向南返贵阳,他在黄平等地寒武系地层中发现很多朱砂(辰砂)矿点,龙里泡木冲三叠系灰岩还有石油显示。他跑这一大圈也有不少收获。
黄汲清回到贵阳时,丁文江一行已于不久前经贵阳北行。黄与他们约定在黔北遵义聚会。聚会后,彼此交谈了考察之经过和收获,高兴地休整了几天,又向东到湄潭、绥阳再向西北到达桐梓。丁又派黄与曾再作一条辅助路线,就是向西北到习水县温水镇,再向东北到四川綦江县赶水镇。他们胜利完成任务,与丁、王相聚,再一同向北到达重庆,下榻于重庆青年会。然后他们准备返回北平。据了解,由于蒋冯闫中原大战的关系,当时经汉口返北平不太方便,于是,他们购了颐和公司的船票,直抵上海,再由上海乘海轮到天津,转火车回到北平时已是1930年的7月初了。
北平两年的苦斗
黄汲清与丁文江、曾世英、王曰伦返回北平西城兵马司地质调查所后,向翁文灏所长作了详细汇报,然后又和总务处长周赞衡、陈列馆负责人徐光熙、图书馆长钱声骏,以及古生物室负责人计荣森等交谈,了解各方面情况,准备开展下一步工作。他们首先要料理因公牺牲的赵亚曾先生的后事。他们见到了赵先生的父亲、弟弟裕曾、夫人和三个孤儿。当时长子松岩12岁,女儿梅岩9岁,次子竹岩尚在襁褓中。为解决赵先生亲属子女的生活教育问题,丁先生、翁先生亲自出面张罗,募集基金。由中国地质学会募集捐款,设立“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以基金每年之利息奖励从事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有突出贡献之学者。从1932年至1949年的18年中,受奖者共22人。1932年首次获奖人即是赵亚曾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他最后一次出差的同伴——黄汲清。当时赵先生长子在农村上小学还未毕业,黄主动承担责任,让松岩与他同住一屋,照顾其饮食起居,还请人帮他补习功课,松岩后来考上了天津南开中学。
黄汲清参加了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在外出差16个月,搜集了丰富的宝贵的科研材料。他首先坐下来研究的便是与赵亚曾先生一同搜集的秦岭山区和四川的地质资料。他先编了一本秦岭地质图册和一本英文说明书,翁文灏所长特派绘图员侯峙先生为他提供地形底图,协助他完成图幅编绘。为写英文说明书,他在原有英文基础上,特别参考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Baily Willis)的《中国之研究》(Research of China)学习其文法及修辞。文稿经丁文江先生审阅,丁又转请燕京大学教授英国人巴尔博(Barbour)再阅,巴尔博见黄英文熟练,且有自己的遣词造句特点,所以稍作润饰就交付出版。该著作为英文专著,名称为:《The Geology of the Tsinglingshan and Szechuan》(秦岭与四川地质之研究) ,作者:Chao, Y. T. & Huang, T. K.(赵亚曾,黄汲清。黄把赵亚曾列为第一作者,一方面体现出他尊重事实,尊重合作者的劳动,因为这篇文章的材料中多半是赵亚普收集的,而且赵亚曾在文章内容的构思上也的确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钦佩和怀念。这与地质调查所在院内东墙与图书馆之间给赵亚曾建了一个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一样,让赵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这篇文章于1931年初作为地质调查所主要的系列出版物“地质专报”(Geological Memoirs)的“甲种”(Series A)第9号正式出版。此书正文为英文230页(附中文摘要48页),随文附图45个,书末有19个图版,另附一本图册,内包括3张1:40万彩色地质图,13张1:20万彩色地质图,两张1:20万剖面图。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黄汲清生平还是第一次,他以后出版的专著也很少有这样规模的。
1931年,黄汲清没接到另外的出差任务就以室内研究为主,消化野外搜集的资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西南地质大调查中,遇见的地层多半是二叠纪的,地层内还有很多化石,最主要的化石是珊瑚和腕足动物,而且他和其他地质工作者在全国各地也采了很多化石,化石标本上都附有标签,写明了化石的产地和层位,化石经准确鉴定属种名称后,就可用于地层划分对比。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收藏的世界各国的古生物学、地层学专著、参考文献也很丰富,其他辅助部门如磨片、照相等也很得力。黄首先在葛利普指导下,研究了二叠纪的珊瑚化石,不仅有他自己采集的,还有丁文江及其他地质学家在全国各地采集的,有些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黄汲清从1931年初就开始研究,并写出了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他注意到,二叠纪地层里的腕足类化石比珊瑚化石更多,于是他紧接着研究二叠纪腕足类化石,用了几个月时间,又完成了《中国南部晚二叠纪腕足动物化石》著作(分为上下两册,英文正文约270页,中文摘要5页,另有20个图版)。然后,他又来研究二叠纪的珊瑚化石,当时他的北学学长乐森璕正好写成了《栖霞灰岩珊瑚动物群》一书,黄增加了西南数省二叠纪珊瑚化石若干新材料,与之合成为一本新著:《杨子江下游栖霞石灰岩之珊瑚化石》,作者:乐森璕,黄汲清。乐森璕为第一作者,反映出黄汲清对学长的尊重。以上四本古生物化石专著,都于1932年分别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的第8号第2册、第9号第1册,第9号第2册和第8号第1册的编号正式出版。
这期间,黄汲清还编制了我国南方二叠系地层对比图和古地理图,其中标明了所含动物群的特点,1932年他完成了《中国南方二叠系地层》专著,该书同年以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甲种第10号名义正式出版。这是国内断代地层学的第一本专著,深受国内外地质界重视,被纷纷引用。这本书加上前述四本《中国古生物志》,为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奠定了的扎实的基础,所以他也得到“黄二叠”的光荣称号。
黄汲清在专心研究古生物地层学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区域地质学、构造地质学。1931年5月,他随翁文灏所长去南京,出席在中央大学地质系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八届学术年会,他在会上宣读了“秦岭大向斜之迁移”的论文,颇受欢迎,当年即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0卷上。后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所长领导的南京栖霞山的地质旅行,收获很大。
国家的命运也牵动着黄汲清的心。1932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给十九路军捐款。黄汲清和同事、青年地质学家们天天看报,了解战况,当得知我军打胜仗时,就高兴地庆祝,他为十九路军捐献了50块大洋,还收到蒋光鼐将军的感谢信。当时中国向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中国,国际联盟派由英国人李顿爵士(Lord Lytton)率领的国际调查团来我国考察。在北平,丁文江先生参加了接待李顿爵士的活动,极力表示友好,希望他们主持正义、为中国说话。黄汲清写的《中国古生物志》中有很多描述腕足动物化石的内容,其中有很多“李顿介”(Lyttonia)标本,壳饰很壮观,这种化石最早发现于印度盐岭,其属名是为了纪念在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李顿而起的,这化石在中国也大量出现,黄汲清发表的晚二叠世腕足动物化石图谱中有很多“李顿介”。丁文江先生让黄把那些图谱复制若干份,赠送给李顿爵士,也就成了“科学外交”的工具。
黄汲清尊老敬友,他与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大科学家频繁交往,彼此十分熟悉。黄汲清192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地质调查所四年间,前两年多投入野外调查,后两年则潜心科研著述,年仅28岁,就发表了六本专著(两本《地质专报》,其中一本与别人合著;四本《中国古生物志》,其中一本与别人合著),不到而立之年,能有如此成就者,实不多见,因而深得丁、翁重视。那时在北平研究古生物化石的地质学家中,还有不少是黄汲清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同学如孙云铸、俞建章、乐森璕、裴文中、计荣森等,他们对黄的聪颖、勤奋、能干都十分钦佩,黄汲清还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切磋,收获颇丰。
丁、翁极其注重培养后学,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而且大胆擢拔青年新秀。两位先生也是刚留学回国20多岁就担负起祖国地质事业创始和开拓的重任。他们对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家——地质研究所的“十八罗汉”中,最看重年龄最小的谢家荣(入学时15岁,毕业时18岁),而谢家荣最后真正是十八人中成就最大者。北京大学培养的学生中,他们最看重赵亚曾,赵英年早逝时,他们悲恸不已,丁在悼亡诗中写到:
“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金骨,化作天南万里尘?……京洛相逢百载期,相知每恨相交迟。论文广舌万人敌,积学虚心一字师。……”
翁文灏的悼文中也有这一的内容:
“青年学者中造就如此之速而大者,即在世界科学先进国,亦所罕见”。
如今,新的接班人影子似乎又出现在他们眼前。
1932年上半年,翁文灏所长要求黄汲清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去欧洲留学深造。当年4月,黄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提交了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攻大地构造学两年的申请。同时,黄又专门请老师补习德语,进步很快。一天,黄去地质调查所谢家荣办公室谈工作,碰到了一位青年,谢介绍黄与那位清华大学的学生程裕淇认识,他们交谈甚好。这是黄与程的初次会晤,以后几十年里,他们成了事业上的密友。当年6月,他从外交部拿到了去欧洲留学的护照,当即去东交民巷瑞士领事馆办签证,他被告知中国人去瑞士不需签证,把旅费用完就回来好了。不久,黄告别北平师友启程,临行前拜访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所长和其他友人,又给四川老家写了封长信,说明要去瑞士深造的事。他乘快车到上海,7月份即乘法国邮轮“波尔托号”(Porthos)离开上海,奔向遥远的异国求学。
(未完待续)
自定义HTML内容